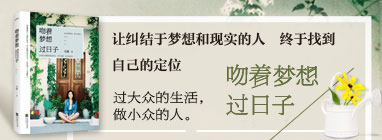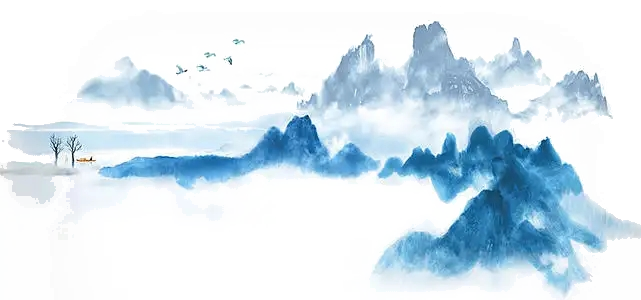涌动枝头花向明,陌野菊花芬飞清。
千山雨寒我独秀,万壑雪飘笑衰荣。
侧身一地风声远,仰首自在香魂宁。
纤茎碧透天边去,回眸一笑芳随行。
——野菊
没有哪一种花能像野菊一样从春笑到初冬吧?!
迎着乍暖还寒的春风,野菊花如小草一样吐绿发芽,蓬勃漫延,迎着阳光,举起一朵朵白的、黄的、淡紫的、浅粉的小花,心无旁骛光明磊落地绽放在枝头,直到凛冽的寒风怒吼着收去它灿烂的微笑。
野菊花,或绵延于陌野,或仰首于树旁,或匍匐于瘦径水岸,或争俏于悬崖峭壁。
一场雨,一阵风,一朵祥云,就能催开一簇野菊花。
那雨,只要带了春意,那风,只要含了温情,野菊便追着流云潇潇洒洒地开了。它不只属于秋天,明媚的春,火热的夏,都有它的芳踪,如果冬阳能够暖暖地照着,它照样付以欣慰的笑脸。比那秋天中欢笑的家菊,更多了一种风情,多了一分光鲜。
野菊花,它把大地母亲的滋润,蹁跹成了花的青春,体贴入微的香。即便到了寒冬腊月,热乎乎的水中,野菊也会手拉着手,氤氲茶汤的清气,用款款深情,温暖风雪赶路人。
野菊花的模样并不可人,花香也微乎其微,如果不是近年来大家讲究“生态”,讲究纯天然的健康,谁也不会在意野菊的生长和夭折,见它,如见一杂草,可有可无,可踩可摧,可拔弃。然,野菊不在乎冰冷的漠视,不在乎人们的欺凌,茎折了,叶绿着,花掉了,梦香着。卑微不卑下,百折不挠,坚强地面对挫折和不平,始终微笑着顶起小花,执着着美的追求和价值。
微风每吹拂一次,清瘦的野菊就长了一分,它不会举起旧年的忧郁,也不会因花朵太小而羞涩,只要有一个虔诚的眼神,野菊花,就情切切地盛开在广阔的视野,开得如此认真,如此磊落,象模象样地哼着青春的歌,唱着天地得失两相宜。生命如此,怎不让我喜欢?!
谁说花无百日红?野菊花就让它细小而又平凡的花朵,一朵追着一朵地开放,直到冰天雪地中,还在枯枝上摇曳着不屈的黄和白!“王孙莫把比荆蒿,九日枝枝近鬓毛,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
记得我在航空发动机厂的大山里上小学时,有许多叫菊花的同学。山里人特别爱在女孩子的名字里加上菊字,因此,我们班里就有了曾菊花、夏菊花、佟菊花、叶菊儿、欧阳冬菊、徐菊艳、徐菊丽……小名则一律是菊花。如果老师喊一声菊花,立马就有十来个稚嫩的应声。那时小伙伴们还问我:“你为什么不叫菊花呀?你的名字不好听!”为了这,我还跟妈妈闹过,自说自话地为自己取了个名字——张冬菊,并慎重地写在作业本上。
老师来家访了,她摸着我的头问:“大生,你知道山里的女孩为什么喜欢叫菊花吗?”我摇了摇头。老师说:“山里人的生活很艰苦,医疗条件也差,特别是女孩子,生了病一般不会去医院看的,都是自己上山采点草药来治。因此,因病夭折的很多。可山里人也希望自己的女孩子平平安安地长大,所以他们沿用了古老的避邪方式,给女孩子的名字中加上菊字,希望她们能像野菊花一样无所畏惧地生长,做到凛冽扫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似懂非懂地望着老师问:“什么是凛冽呀?”老师说:“凛冽就是很冷很冷,到处都结冰凌柱,风刮在身上像刀割一样疼的寒气。”我点了点头。老师又说:“大生,你的名字也很好听,你的爸爸妈妈也希望你能像野菊花一样,在天地间百折不挠地大长大生!”
那一刻,我快活地跳了起来。老师问:“还改名吗?”我坚定地回答:“不!”然后,拿起橡皮擦在作业本上擦去了改的名字。老师再次摸了摸我的头道:“大生,名字只是一个寓意,重要的是你的品行要像野菊花一样坚韧美丽!”我不全懂,但“美丽”这两个字是每个女孩子都心领神会的。
后来,我去城里读书,还不忘启蒙老师的这席话,很搞笑地指正同学:“不是野火烧不尽,而是凛冽扫不尽!”
这席话,让我受用了一辈子,即使是文革,许多同学追着潮流改名,我也没动过改名的念头。
从那以后,野菊花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春天,我会走进陌野山中,采一大捧粉、紫、白的野菊花,配上红艳艳的映山红,放在斗室里,令蓬荜生辉。秋冬,又将野菊配上大朵的菊花,让清香的菊魂飘逸在心的周围。
野菊花不为妩媚而来,谦谦君子,静守着淡定和从容,完成了从孕育到极致的绽放。也许,在它的世界里,保持着美丽的微笑才是健康的生活态度。所以,它不怕贫瘠,不怕寂寞,不在乎风刀霜剑,也不虚伪好面子,面对挫折,它不会改变志向,留下的是铁质般的心音:“明年,我依然绽放!”
啊,野菊花:
不叹冷风刺骨,乐悠悠,笑颜常驻。
敢问凛冽几度?满怀情愫,香魂不愁去处。
伴明月,傲然雪中度,读君风光,晶莹剔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