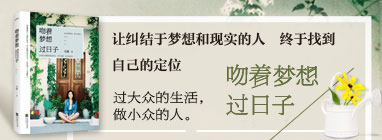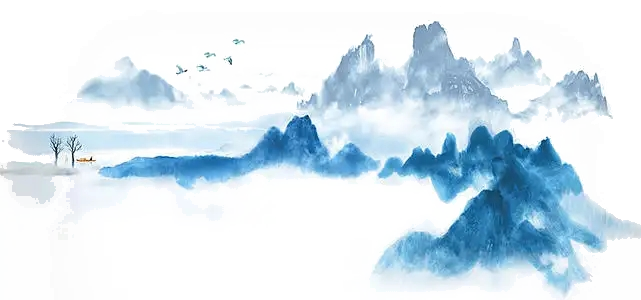听,是谁在呼唤,还是你心底的盼望,响遏城市上空的云霄,像候鸟一样穿越季节和海洋。
这个冬天,一曲破晓的哨声冻在原处,一直等我吹口气,再度响起来。
人走在不同的地方,踽踽凉凉,在不同的时光,看窗外日月跑马,催生了不同的孤独况味。
起床的铃声催逼着一直沉睡着,淤积着,荒芜着的肉身,睁开眼,窗里窗外一样的暗昧,电灯的开关挑起暗昧的竹帘,半梦半醒间,习惯了为那些喊饿叫渴的神经准备早餐。
夜还没有撤销它的专制,流动着空气的寂静。猝不及防地,几声清脆嘹亮的口哨从楼下响起,黎明的寂静成了扩音器,无限放大地在六楼的窗口吹送。陡然间一激灵,醍醐灌顶般彻底醒透,手脚机械地忙活着,心儿已被哨声唤走。可是,多么短暂啊!美妙的哨声已戛然而止,随着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我无缘一见,一心追上的那个现代骑士已绝尘而去。
那份泪涌的激动还在,破晓的哨声吹彻一股一股晨曦的寒风,暗昧随之退后三尺,光明的惊涛暴涨了三丈,无形的云手反复推就之间掀起幕帘。窗外渐渐能看见带点透明的微光,头顶上的青天还未曾蓝的放肆,半灰半蓝,似明似暗,但冥冥感到了人力的推涌,暗昧在轻悄乖觉向后退缩,黑夜释去了夜间的兵权,人随着淘气的星子跳出捱时光的旧习。即使昨夜的深蓝给黑夜带走了,也期待着要在新的阳光中取得崭新的蓝色,昨夜今我一瞬间,时光不容庸人自扰似的。
口哨声像一滴清露,滴在城市这朵将残未残的金菊花上。
这时,白昼开始无限地旋落,声光色从四方浮来,有层次,有秩序,楼层显露出面与线平铺直叙的几何,玻璃幕墙分割着人目盲五色的视觉极限,生活又沸腾的像一首交响乐。
洪大的声音碾压、覆盖了口哨声,我躲在楼层的“山洞”里倾心领会,哨声和那些巨大乐器的碰击,并无限放大地回荡在寂寞的“山洞”里。它不同于夏夜池塘里的蛙鸣,也不是秋夜寒蝉的凄切,更不是手机订制的教堂里的钟声。那种率性而为的快意,让人似乎探测到阮籍和向秀打铁时侠骨之香。
在没有乐器的远古,人类也是发出这种声音赶走黑夜的吧。
破晓的哨声,这是所有声音中,最好听最美妙的人之声。
这个吹哨人也许并不知道,哨声已注入别人的生命,像清晨气质的诗歌注入生命一样。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引醒的已不是一向由晨鸟引醒的因素,尤其破晓时的存在,显得多么陌生新奇,以古老的荒蛮激情回近于宇宙,回近于人类自身。分裂飞扬的人意峭厉地一扫我无为的寂静,而在可爱的有为的寂静里,人才有勇气有精神爬到更高的地方,以崭新的姿态,童真的目光为惯看的风景重新命名,哨声一路伴我抵达阔远的光明之境地。
一段时间里,那被温柔之乡抚育过初醒,总是支楞着耳朵倾听,想擒住那哨声。窗外大海一般的阗寂,深渺,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我把那划破黎明的哨声当做稳固的陆地。听觉出奇地敏感,出奇的敏感的绝望者才渴望听到大地醒转,精进鹰扬的哨声,在不容旁骛,不可方物中才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
哨声也像一些偶然的微茫的变幻吧,在自己特定的生命里尘埃般升降落定。打捞着哨声星沉的余韵,我懊丧地伏在窗口,荏弱的像一个被哨声遗弃的人,一生别无所长,只是一颗心几近于寒冰,常做无焰的燃烧。可我分明又幻听到哨声抵门的声音,像日光一样毫不客气地占领了每一个房间,到底是我住进了哨声里,还是哨声油然不形而神地吞没了我的“山洞”。
那哨声有无数种版本,就有无数种的变调。是沈从文在《静》中,回荡在老城墙上的捣衣杵声,小尼姑对着河水喊自己名字的天真回纹,这些避其锋芒的生趣远远高于战争剑拔弩张的颐指气使。
望着一卷在握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甚至怀疑年轻的克利斯朵夫带着前程无限的潜力重返人间,吹响“我才知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的飞扬跋扈。
他又何尝不是个凡中之凡的汉子,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深情,一肩风雨一肩烟火任平生,以我不知道的步伐,走向我不知道的未来。这伴着他继续行走的哨声里,岂不也有属于他的位置,属于他的谦卑、尊严、快乐?属于他能掌握的,一方完整坚实的小永恒?在庞大无期的现实面前,那嘬起口唇的自信与愉悦,或许正是他一生无惧且无憾的地方吧。
一眼望开,想象可以无限地延伸,兴亡悲欢,是非成败,金戈铁马,百年登临,独系夕阳缆。也许正是那位自甘天地一腐儒的诗人,虽不曾夜里挑灯看剑,耳畔却回荡着边塞将士的鼓角争鸣,西风残照下的马嘶,大旗,国破山河在。犹是,历史的长河里独一无二地蹁跹着字子美的一沙鸥。
噢,不!——发出哨声的人不需要身份,意气何须论功,哨声永远比身份高贵。
雅韵俗奏长驱直入,纷沓而来的意象还在挥帜啸聚,却原来,安东尼奥不断切换的镜头里,都是内心不断地酝酿的许多感觉,因外在的哨声勾引出来,于弄笔之际,一切形迹周旋的不能止息。
其实,我多么想以此为嚎啕大哭的悲剧英雄拭泪,真心地捧上桂冠上的钻中之钻——破晓的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