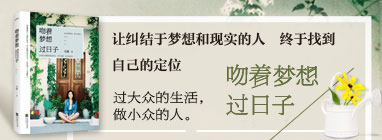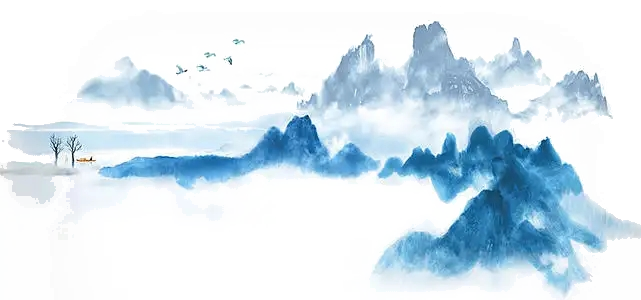文/幺幺0
主播/文珂
美工/彩韵
现在是2015年6月6日北京时间十七点二十一分。挂掉电话后,我简单的披了件外衣,倚在窗边看雨后回旋的老燕,又到了它们忙碌的筑巢时节。燕子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往复而来,带着死亡的迁徙只为了繁衍,疾风骤雨间的穿梭更像是对爱忠贞的承诺。只是年复一年,老燕去,新燕回,生于他乡,死于故土,难免一生漂泊。呆立了一会,想起刚刚的电话,便自嘲的笑了笑。别人的幸福与难过,我们尚且看不清,又何况那些没有束缚的燕子,人们总觉得自己清明,看透了你对我错和世间善恶,可人心沟壑,有哪里是简简单单的评判对错。
电话是蓝涩打来的,没错,就是梅雨公寓一中那个穿着红色帆布鞋的蓝涩,蓝天的蓝,苦涩的涩。我们之间绝算不上相熟,大家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肯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时,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床上为彼此间毫无隔阂而坦诚相对,一种是在江湖因彼此间足够陌生而放心倾述。显然,我和她之间属于后者。接到她的电话我很惊讶,我的故事她并不知道,仅仅在离开时简单的告知,再加上我不太喜欢摸不准内容的交谈,于是迟疑了一会儿。可是说实话,对她,我有愧疚有敬畏也有些更深层的情绪,这些让我没有办法挂掉电话,最后还是接听了。她没有寒暄,我也没有说“您好”,对话很简单。
“想去看望你,方便么”
“什么时候?”
“7号8号,两天”
“好,定下来到的时间,我去接你”
然后,是将近一分钟的沉默。就在我想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又说:“我们之间算是朋友么”
“算是吧”
“朋友之间,可以撒谎么?可以漠不关心么?可以去看你时不带礼物么”
我握着手机的手不自然的抖了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心里想:难道,她已经知道了?就在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时她又说
“对不起,曾经我讲的那个故事里,有谎言。对不起,知道你生病,半年的时间里却一直不闻不问,对不起,我只是好累,快要坚持不住了”说着,我隐隐听到了哽咽的声音,担忧的同时也放下心来,原来,她并不知道我的谎言。
“你知道什么是朋友么,不是相互利用,不是嘘寒问暖也不是坦诚相待。朋友,就是那个你想和她一起玩的人,想从早上玩到晚上整整一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想着明天接着一起玩,就这么简单”
又停顿了一会,她应该是整理整理了情绪,才语调轻缓的说“好,那明天见,这次,我再讲个故事给你听……”
夏天的时候,晚上七点,天开始暗下来,我坐在阳台的小凳上,想起了两年前的事。其实,遇到那个穿着红色帆布鞋的面孔可以说是巧合,然而进一步与她熟识却是我深思熟虑的预谋,只因为,那张面孔,不是第一次看到,一如真相里,我先遇到的不是蓝涩,是蓝琴。
我讨厌在我写的故事中说谎,所以梅雨公寓一,仅仅是选取了一些片段,远远没有歪曲事实。例如:我写到了13年南下去普陀山在宁波时辗转去了毛竹庵,庵里面有一个女孩儿,没写到是,她叫蓝琴。我写到了那一夜荒山寺庙里满心的恐惧让我整夜未睡,没写到的是,没睡的原因还因为蓝琴给我讲的故事。我写到了自己坦诚接受了蓝涩关于妹妹与有妇之夫远走海外的断言,没写到的是,蓝琴其实只身离开,一路向南。今天,就讲所有的真相给你听。
那天和今天差不多,也是落日后,我和蓝琴对坐在毛竹庵中的石凳上,第一次见面,难免生疏,讪笑着和她问过庵里情况后,不知怎么就问起她来这里的缘由,这一问,让她脸上轻笑的表情僵住了,好半天,叹了口气,才说“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这里,讲给你听,也没有什么,要不也就烂在肚子里了,就是,挺无趣的,也挺长”。听过她的话,我指了指庵门口的黑狗,笑着说“想到它我就睡不着,哈哈,你讲吧,我听到天亮”。
“我叫蓝琴,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叫蓝瑟……”
小时候,爸爸妈妈忙,她们在姥姥身边长大,老人家年纪大了,难免有照看不到的时候,再加上她们两个脑筋活络,就淘气的紧,三天两头就折腾出点幺蛾子,不是踩坏了邻居的黄瓜秧,就是把大黄狗扔到猪圈里,更有一回,两个人爬上了房顶,在烟筒里塞了团旧抹布,那天家里冒了一晚上的浓烟,每个人都像钻过矿洞一样,灰头土脸的,她们躲在院子里偷偷的贼贼的笑。小孩子做坏事哪有不被大人发现的,被发现就免不了责问,通常都是妈妈掐着腰喊“说,你俩谁干的?”每当这个时候,蓝涩就愧疚的地下头不说话,蓝琴反而小眼睛滴溜溜转,蹑手蹑脚走到妈妈身后,小声说“妈妈,我给你讲啊,从前,有个小孩,她说黄瓜是害虫,要扼杀在襁褓中,从前,还有个小孩,她说,大黄和小花猪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应该让他们团聚,从前,还有还有一个小孩,她说,老师讲董垂瑞炸碉堡,我们要像英雄学习,先干掉会冒烟的东西,从前……“还没等她下一个从前讲出口,妈妈已经一个健步穿出去,抓过蓝涩,开始胖揍了。蓝涩还是低头,不说话,疼了也不嚷,只是轻轻抽噎。
第二天,蓝琴拿着个豆沙包找到依旧在屋后罚站的蓝涩,扯了扯她的衣袖,不太好意思的说“那个……姐……对不起啊……不都说丢卒保車嘛……你看……坏注意都是我出的……我就是車呗……那个……你……你还疼不?”蓝涩还是低着头不说话。蓝琴慌了,手里的豆包扔到地上,双手拽着姐姐的袖子,眼眶泛红,眼泪汪汪带着哭腔的喊“姐……你别不理我啊……我错了……以后换你讲,你就讲,全天下的坏事都是小的干的”。这时蓝涩才抬起头,那张青涩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怨愤,竟是满眼的宠溺,她扬起另一支手臂,揉了揉妹妹的头,笑意吟吟的说“从前,有两个小孩,全世界的坏事,都是大的那个干的,小的是笨蛋,只会哭鼻子,鼻涕都过河了,埋汰鬼”。正午的阳光越过专属于那个年纪斑驳的印记,照落在妹妹那张破涕为笑的脸上,鼻涕挂在嘴角旁,亮晶晶的,晃花了琴瑟和鸣的脸庞。没人注意到,掉在地上的豆包,黏满了泥土,被大黄轻轻叼走了。
随着年纪长大,姐姐沉稳妹妹活泼的性格就愈发明朗起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姐姐喜欢大提琴,而妹妹喜欢小提琴。音符的节奏,高高低低断断续续陪她们走过了花雨季,再抬首,姐妹已经上了高中,那一年,她们各自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抉择。父亲从商妈妈持家,这些年过来,虽不是大富大贵,却比平常人家宽裕些,然而,提琴相伴的生涯不得不随着父亲生意的失意而中止,与之而来的是,家中仅有的积蓄,仅仅能够维持她们其中一个人继续走艺术路线的可能,也意味着,必须有一个人放弃,回到常规高考路线。父亲叹气,母亲含泪,没有人能给她们判定一生的言语,只有她们自己,四目相对,沉静的眼睛对上活脱的眸子,没有人说一句话,各自回房间关灯早早的入睡了。谁也不知道当天晚上发生过什么,只是从此之后,家里不再有大提琴的影子,小提琴的声音总是在深夜响起,奏出某种固执的愧疚,台灯下,蓝涩伏案读书,桌角玻璃瓶中清早插进的鲜花,悄悄枯萎。
蓝琴去参加艺考的前一天,姐姐床头给她放了一封信。蓝琴说“我甚至能想到她写这封信时的表情,一定像是小时候在墙边揉我脑袋时的宠溺,信里蓝涩写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梦想更是两个人的心愿,希望我能满怀力量,还说如果我失败了,她陪我去街头卖艺,来一场姐妹勇闯天涯。可是,你知道吗?她从来就是比我优秀的那个人,她的大提琴水平,远远高出我的小提琴技巧,那天晚上,我偷偷出门想扔掉小提琴,却在外面看到了哭着砸琴的她,边砸边说——妹妹才是琴,琴瑟的琴。也是那一年,她改了名字,从琴瑟的瑟到苦涩的涩”。
而这一切,却只是开始。蓝琴在艺考中发挥超常,意外的获得了三个优秀院校的offer,只要高考成绩达标,便可以自行选择,这无疑对全家人都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姐姐更由衷替妹妹高兴着,可与这喜悦格格不入的人,确实蓝琴自己,她开始感到肩上无形的压力——高考成绩。她害怕这一路的代价和顺畅因为最后的失利而付之一炬,因此,在接下来突击文化课的时间里,她开始暴躁易怒,经常发脾气或者哭泣。甚至从姐妹两人的房间中搬出来住到了学校宿舍里,这样的状态任父母焦急姐姐劝慰都不济于是,时间越近,情况越糟糕,结果就是,高考的那天,蓝琴逃掉了。临走前,她指着蓝涩的鼻子喊“这回你满意了吧,别觉得自己慈悲,我不领情!”
蓝琴带着不多的钱,一路南下,去了浙江,那里温润的山水渐渐抚平了她燥热的心,偶然走过寺庙墙外,听到暮鼓晨钟的声音,更让她回归了澄明,翻涌起来的就是满心满眼的愧疚不堪,还不满二十的半大孩子,夕阳下在寺庙门前,放声大哭。哭累了,擦干眼泪,踏上了归家的路。
家中没有人抱怨也没谁责备,她向姐姐哭诉道歉,姐姐依旧笑着应着,满眼宠溺,她向父母跪着磕头,父母却长长短短的叹气,不说什么。她信誓旦旦的和每个亲人保证,一定重新奋发图强,好好努力,明年再考,不会让他们失望。蓝琴以为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她重新变得开朗起来,和姐姐闲逛了整个夏天,直到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
她想问为什么。为什么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蓝琴的名字?为什么没参加高考的蓝琴竟然以优异的文化课成绩考入了三所学校中最优秀的大学?为什么,姐姐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这次,没有人告诉她理由。姐姐不说话,揉揉这个已经比自己高的妹妹的头。镜子中两个人近乎完全相似的脸庞或许才是真相,除了父母,谁也分辨不出他们,连监考老师都不能……
蓝琴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呆着,或者整夜练琴,连邻居都几次找上门询问,她还是不说什么,依旧我行我素。这样的沉默,延续到九月,她拎起行李去上学时。出门前,她深深的看了姐姐一眼,深深的、压抑的、汹涌的、愧疚的、悲伤的、有着很多很多说不清的情绪,唯独没有,感激的。
蓝涩在妹妹走后,重新复读,第二年考入了本市的一所大学。四五年间,妹妹利用假期四处游走,姐姐如常的陪在父母身边,她们鲜少碰面,过年的时候在一起,也没有了小时候的亲昵,多了份生疏,少了份自如。其实,要是能维持这样的平静也很好,可每个人都在长大,在虚拟的获得与真正的失去中亦步亦趋。
生疏后的两个人,已经很少交谈些什么了。就算姐姐知道了妹妹和有妇之夫有染,也没有太多立场去阻挡,蓝涩成熟稳重识大体却也不锋利,她甚至已经习惯了多年的忍让和退避,去放纵那个比自己晚出生半分钟的孩子已然成为深入骨髓的习惯,我想,过分的说,就算蓝琴杀人,胆小的蓝涩都敢替她遮掩隐瞒更或是顶罪。这种宠溺在尚且不谙世事的年纪种下了,就哪里还能分的清善恶或对错,更多的是一意孤行的执着,它不会让人觉得幸福,反而成为了负罪和枷锁,因为姐妹远不同父母,没有先天的生养之恩,这后天的筹码就显得分外沉重,能压垮一个人,压垮一个人的一生。却也没人有资格说她的对错,一切是缘,善缘恶缘随镜而生,因果罢了。
蓝琴在一次偶然见听到了姐姐与另一个女人的争吵,她才知道,姐姐与那个女人相爱,那个人想和姐姐离开这里远走高飞,到一个远离熟人的陌生城市过点平常人的日子。争吵是因为那个女人一再提起离开的事,姐姐却一再拒绝,女人问她原因,她就沉默不答,最后那个女人爆发了,大声叫嚷“你不就是为了你那个妹妹么,你不就是怕她当小三有一天不得好报么,你……”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姐姐拂袖离去,女人俯身痛哭。蓝琴呆立不语。
这一次,她想着,该是自己报答姐姐的时候了,否则这一生的愧疚真的会把她压到窒息,于是她约了男人出来,谈分手的事,不成想让男人的妻子撞破,才有了后来的悲剧。最后,她以和男人远走高飞为由,远离了她,那个赠与了她无限宽容和宠溺的人,那个赠与了她无限愧疚与痛苦的人,那个赠与了她今生只愿遁入空门诚心忏悔的人。
讲完这些,天已经蒙蒙亮了,石桌上茶壶内的水冰凉,我倒了一杯,满口喝下,是从内到外的寒意,直到大黑狗伸伸腰支起身子,天大亮,她才收了望向远方的视线,起身回了房间。而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这个故事只适合讲述,不适合评头论足。你或者我,或者除了她们姐妹外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回忆到此终止,我伸了个懒腰,起身回房间,沉沉睡去。
我从蓝涩那里知道了她来找我的原因和故事的后来。蓝涩的母亲在四月的某一天,沉沉睡去。不再醒来。妹妹爱过的那个男人,夹着尾巴回到了曾经出轨逃离的家,经常满脸笑容的陪着太太在离蓝涩家不远的公园散步,这才让蓝涩知道了妹妹的谎言,她开始慌张,她害怕失去,她宁愿知道妹妹和男人幸福的在远方生活也不愿意妹妹音讯全无。她和我说“我骗了你,我其实隐约知道她没和那个男人走,却不敢去面对,我怕蓝琴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你知道吗?我看过她的日记本,只有四个字——重恩成仇。这两天又是高考的日子,一切像轮回一样折磨着我,我心里一样有怨恨,当初梦想的放弃,虚假的代替和所谓的顾全大局,姐姐这两个字让我好累,想全都放下,却又放不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来找你,你是唯一让我有过片刻平静的人。“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第二天清早,带她去了山上。山上有一个高高的菩萨,每天早晨都会有人扛着香,前来叩拜。
我和蓝涩玩了一个游戏。我们坐在佛像前,猜测每一个来人许愿的内容。
来的第一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面容悲戚。蓝涩说:“她一定是求爱情顺遂”,那个女孩子虔诚持香默念,低头许愿,却在磕头时,泪流满面,周围有人对她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她也不在意,哭了小一会,抹抹眼泪,离开了。蓝涩侧头问我:“人家许愿都不说,咱们这怎么猜?”,我轻微摇摇头回答她“再等等”。
来的第二个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黝黑微胖,头发已经有些稀疏了,圆领汗衫歪斜的穿在身上,牛仔裤很破旧,鞋子沾了些泥土。我侧头示意蓝涩,她想了一会说“高考嘛,我估计他这个年纪应该是来为孩子求学的”。她的话音刚落,就听男人持香朗声说道“祈求菩萨保佑我斗地主别挨炸,多抓王多抓二!”蓝涩刚喝进嘴的一口水,全都喷到了我的身上……我闷笑着擦拭,眼角余光看到了第三个人。
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夫人,应该是染过好多次的头发却还是遮掩不住花白,面色枯黄,衣着平常,只是步子走的很稳健,眼神诚恳。蓝涩加重了语气说“这个一定是求子孙的,或者求儿子官运仕途”。我收敛起轻浮的笑意,对她说“不是”。那个妇人,语调顿挫只有一句话“祈请诸位佛陀保佑,愿此方生灵得闻佛法,身心安康,此间地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蓝涩也收敛起了敷衍神色,严肃起了,继而,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下山的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吃过早饭,我送她离开。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和她说“我们总觉得自己清明,懂礼法知世事尊道德守礼仪,于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左右着我们的世界,其实不是,我们眼中的悲伤或快乐,很多都是像那个女孩一般无名的原委,我们眼中的善意或恳求,很多都是像那个男人一般哭笑不得的愿望,我们眼中的平庸或世俗,很多都是像那个妇人一般出离常规的慈悲,别给自己太多枷锁,世间万事万物,离不了一个自然之法,随缘而至,可能曾经你做了太多强求的事,今天便不开心吧,要是今日能放下,人生的路还长,终究能得个大自在。只有你放下对恶的偏见,才能放下对善的执念,天地中间有正道,和善恶无关,只为因果循环。”
她缓缓点头,和我说“其实,我叫蓝瑟,蓝天的蓝,琴瑟的瑟。谢谢你,让我想通了一些事”。
我说“我知道,曾经的事我都知道,同样谢谢你,让我见证这一场因缘”。
她错愕的望向我,想问些什么。我指了指她身后说“车来了”。
说罢,在她手心放了一个信封,转身离开。
信封里是沈阳飞往宁波的机票和去毛竹庵的路线。之所以是沈阳到宁波而不是哈尔滨到宁波,是因为她往返一路,只是来看我,只有她回到原点,才能清楚的看清自己再次启程该走的路,至于去或不去,就是她的事了。
双手插在裤袋里往家走,边嘴边嘟囔“让你充高人,假大方,没钱了吧,走着回去吧,活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