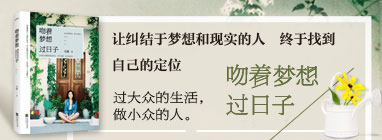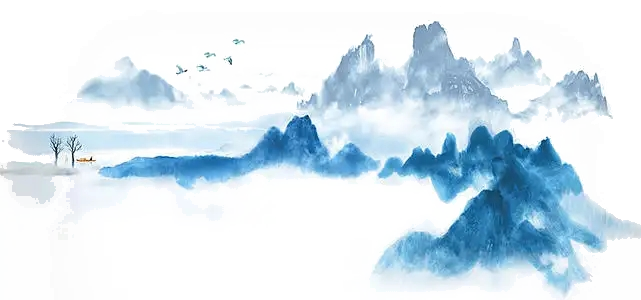放倒椅背,几乎与地面平行,于是可以直视摇曳的绿叶,不过我的疲惫已到极点,无心沾染绿叶的潇洒,只想在狭小的空间里,尽量舒服地安放这付躯体。
把腿伸直,缓冲一下紧张的肌肉,让他们不再承担任何的压力,给他们片刻的宽裕,明显感到肌肉被这突如其来的恩赐惊呆了,它们摆脱了大地和身体的束缚与挤压,激动地战栗着,上下,左右,前后,像拨动的琴弦,久久不能平静。腰和背也放开了,所有的经脉在这一刻舒展开来,血液也无规则地流动,像是倒在桌面上的水,似乎是被风在左右,胡乱的画出一些形状,然后再集中拢来。一张纸被高兴地摊开了,平平整整地摊开了,抹平了所有的皱纹后摊开了。加上鸟鸣和微风,吹跑了两块肩胛骨之间的无形的锁,如同一双翅膀自由地打开,所有的羽毛都铺在身体下面,构成一张毯,或者一张床。青松为笔,夕阳为墨,清风如稳定的手,把树荫下朦胧的倦意书得写意自然。此时,眼睛也要知趣地闭上了,闭上了,看到的也不比睁开的少。先是一团金黄色的光亮在正中跳动,四周的黑暗想要将它包围,像几个黑衣的绅士想要争取一位艳丽的名媛作舞伴,虽然情真意切,但也不强人所难。于是,金色和黑色就在一来一往中左右穿梭,有时增减,有时变形,有时黑色站了上风,将中央塑造成瞳孔般的圆球,有时金色有抢回了阵地,在舞裙上镶了一条金边。时间也像不存在了,也许只有一两分钟,也许过了半个小时,黑色与金色都消失了,形状与姿态都不断变化的灰色占据了空间,也许是灵魂的形状吧,她灵活地绕开了视野的纠缠,总是跑到想象空间的角落里,让你仅仅看见她的裙角,你一朝着她走过去,她又跑去了另一个角落,只留下一个倩影,一个微笑让你去找寻。眼神向左,她就向右,眼神向右,她又向左,眼神也在不断的寻觅中感到疲惫了,也懒得理她,就停在那里,这时她又像个任性的小孩,躲着没人找,自己也觉得无趣,便又走了出来。灰色渐渐扩大,渐渐加深,构成了混沌初开的景象,四周一片沉寂,浑浑噩噩,没有上下左右,到处昏沉。这些灰,也许就是构成宇宙最初的元素,它们布满了整个空间,也包括想象的尽处,以及思维的源头。
四周渐渐出现一点一点的火星,一闪一闪,在黑暗中跳动,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把黑暗慢慢廓开来,有了光,有了思想,如胚胎在母体里孕育。然后一把又一把锁接连着打开了,笼子里锁住的意识被释放了出来。面对着广阔的混沌世界,他手足无措,感到恐惧,像独自游走在荒野里的小孩,他想寻找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小木屋,那便是躯体。可躯体无论如何也不听他的使唤,他想窜到四肢,可四肢却牢牢地订在那里,想流进血管,血管也锁上了栅栏,他小心翼翼地按响了神经的门铃,可神经在屋里熟睡,还顺带蒙上了被子。于是,这个可怜的小孩只能蹲在门口,望着天空,玩着泥巴自娱自乐,等待着躯壳接纳他的时候。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也许很久,也许……
一片树叶带着命运的敕令,被风吹落,径直穿过天窗,轻轻地划过这张沉睡的脸庞,一股强大的电流瞬间通过了躯体,如同春天的生机催生了树木的嫩芽,源源不断的动力从灵魂的最深处流出,黑白灰变成了五彩缤纷,幽暗的林间小路忽然繁花似锦,意识便沿着这边大方地走进了每一个城堡,虚幻又回到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