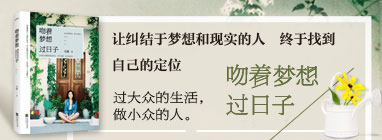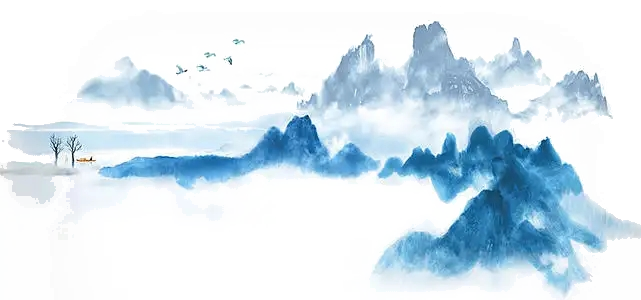一场濛濛细雨把山峦沐浴,蓝空中的白云也如刚刚漂过的丝团游移。青圃柴门,桃疏杏斜,梨黛柳绿;溪畔阡陌,清空润馥,山高影底;蓦然抬眼,撞怀梅红粉颦,一时惊诧:昨日素襟袖,一夜着綺裾。细目哂之,无怪唐朝诗人薜维翰作《春女怨》:“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得入来?”品味钟嵘所言“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是也。
总以为,花是美好的象征。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由物及人,借桃红咏叹青春少女,妙在佳处。“灼灼”叠字更给人以照眼欲明、美人倾慕的共感,而时下令暖梅华,乍然春绪蒸蔚,连肺腑魂魄都成了花仙的领地。不禁油生“花开总有意”的牵思,难道是梅子“心悦君兮君不知”吗!
这青圃之地,不敢说是厮守的閨土。但四时总留下我的身影,若乔卉有思,诗文歌谣早已化为晨粉晚香。那梅子、桃妮、杏娘、梨“旦儿”在心中已然是“梅妻鹤子”,但为什么凝香不露奇,华浓妃出浴,“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呢!
转念,花其实并不是附庸风雅的女子。不是“思君即幽房,侍寝执衣巾(汉·繁钦《定情诗》)”的人,宋女严蕊说“花开花落自有时”。“三月清眸看,兰若空林色”,不过是审美者给花强加了感情色彩而已。也许“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那么,花的本心又是什么呢?
一冬的静养,一季的积蓄,一岁的反思,一时的绽放,让人派生无限怜惜。唐严惮千年前就提出这个命题:“春光搏扔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我只能说,那是生命的灿烂光华。
诗经·小雅·《苕之华》有句:“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同样是赏花,却与《桃夭》产生截然不同的审美感知,从兴花到忧生,此花与彼花就真的是“本心”的差异么?
西方的马丁·海德格尔创立了独特的“存在美学”,认为“只要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为此,我思忖,或许花开就是西方接受美学里的“文本”,人们欣赏出多种多样的感知。那么,我视花子君,执意衷情,怜其爱之所爱,是否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呢?
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通灵之花,感其所发;这或许就是生活,或许就是生命的存真。
梅花乍吐是春天的物象,生活美好是人们的希冀,生命崇高理应得到礼赞。禅悟,花开是其物种延续的必然,从生命角度观赏,当是自然的绮丽。人无论生忧知乐,皆是生命之花。不过,我总爱花及思,憧憬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