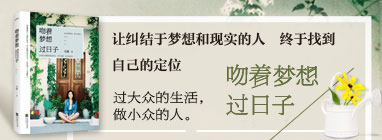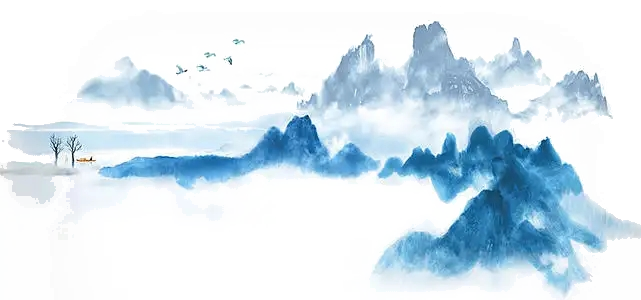是在我凝神,读着黎戈笔下的阿赫玛托娃的时候,窗台外,传来一阵如风如浪的雨声。
那种光景,来了就是来了,不由分说,难以幸免。
这种时候,如果独自在人间踯躅,少了一件衣裳,少了一把雨伞,或者都是心惊胆战。
走在寒凉里,人的牙齿打颤,仿佛是牙齿在意乱情迷跳踢踏,狐步,或者恰恰。
小城多夜雨,谁一言道破天机,道破心底的秘密。
一个人,是极其容易在静夜里雨声潺潺的,恰似木心在冬日里大雪纷飞。
为之心动过的某个人,令你心生温暖的一句话,或者半明半暗的一条街,路旁一棵独自亭亭,开满花的树,都让你的心,浮起一阵一阵的浪。
潮起潮落,那最后的一阵余音。不澎湃,不汹涌,不喧哗,不骚动,兴奋的,知道偃旗息鼓,叫嚣的,知道万籁俱寂的妙处,年轻的都已年轻过,沧桑的依旧前路踟蹰。
此刻唯有宁谧,唯有恬静,幽幽藏着一股轻盈的翕动。是蔡琴歌里的“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没有年轻过,没有过一段深深浅浅的忧伤,与水到渠成,柳暗花明的沧桑,没有在烟花下眩目,继而在静夜里垂泪过,没有为一个人闻鸡起舞,心旌摇荡,而终于守口如瓶,秘而不宣过,又怎能明白,何为“浪花的手”,如何懂得珍惜,岁月弥深里,一种只与过往相关的恬静温柔,一种牢牢实实,安安稳稳落在心底深处的,山长水远无处相逢,却永久鲜亮,不会变质的,你的温柔。
睡梦里,也是一场雨。一场突如其来的夏季的雨,拍打着阁楼的阳台,和阳光一道洒下来。人是晕眩的,恍恍惚惚的,落了一身的汗,仿佛心里也在下着雨,它不知该如何上天入地,落入尘泥,只好偷偷地,从肉身深处往外头沁。
青春时候的人,总是半梦半醒的,一半小心翼翼的精明,一半恍恍惚惚的痴迷。也不知是在等着谁,是在等着某一个季节,还是在等着一朵花,抽丝剥茧,不为无人而不芳的偷偷显山露水。
但终究是盼着一个人来望,一个人来赏,一个人来把这秘密公诸天下。
而那人呢,往往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五个字,令人摧眉折腰,令人绿肥红瘦,令人徒然生出了皱纹,此夜落红无数。
青春时的雨,下的何尝是雨,是雾,而是青春,是情念,是寂寞心事化为千片万片,散入春风满洛城。
记得,曾几何时,有人说过,青春是你最鹤立鸡群的资本,不要辜负,不要奢侈浪费。
我只报以清浅的一笑,我何尝敢谈及青春,那仿佛是别人的事情,我这里,只有两句歌词,“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哪一年,让一生改变”,“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耻于承认,抑或腼腆不承认,一个人心的渐老,他自己最知根知底,最深不可测,不与旁人相关。
我便隐隐地觉着,窗外的雨声里,含着落花絮絮的声响。一种幽咽,幽咽泉水冰下难,一种静悄,笑渐不闻声渐悄,一种萧萧,无边落木萧萧下,虽然,也不至于那般轻狂。
我仿佛应该忆起林黛玉,这多情葬花的女痴,但偏偏不是,我反而忆起了三毛,这个走天涯,心坦荡的女子,赤裸地爱过,失意过,但她终究是无怨悔的。光这一处,她已然是女杰。我忆起的,是她与亲爱的丈夫荷西住在异国时的一个小插曲:
“那天他在我窗外扫地,风吹落的白花,这老人一朵一朵拾起来。海风又大吹了一阵,花又落下了,他又拾;风又吹,他又拾。这样弄了快二十分钟,我实在忍不住了,光脚跑下石阶,干脆把我那棵树用力乱摇,落了一地的花,这才也蹲下去一声不响的帮这疯子拾花。”
是从这一刻起开始喜欢三毛。
她说自己是势力极了的人。然而,我偏爱这一点真性情。
我们爱过,又被爱过,我们哭过,又若无其事地,或者如火如荼地,再笑回来,我们梦了,魑魅魍魉,或者安然无恙地醒来了,看着天明的光,双手捂住面庞,我们所能守持的,弥足珍贵的,不容易为人攻破,为世道糟蹋的,不过是这一点“真”,别人不明白,自己不能不珍重。
如此,亦舒那一句惊艳四座的妙语,可以稍续。我要有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给我很多的钱,除此外,我还有健康。其实,我们还有那一点自斟自酌,自哀自乐的真。
青春过去了,梦中人已远了,雨季不再来了,梦里花落知多少了,万水千山走遍了,我们不能不自己珍重,至少还有那一点点真,要牢牢守着,要颠扑不破,要敝帚自珍,否则便是一败涂地,一无是处了。
这样,至少归去,归去,归去时,还有一川熟眉熟眼的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