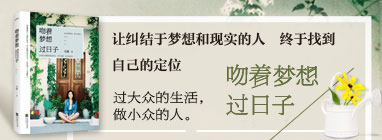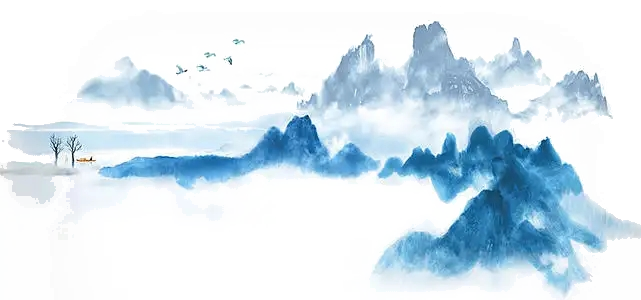窗外的那棵石榴树,刚淋过雨。雷雨咆哮里把记忆燃起
犹记得小时候家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梨树,另一棵当然不再是梨树,而是一棵石榴树。
小时候的院落不像是现在乡下的高围墙红大门,一个个的把自己围圈起来。那时候家里还是低矮的墙头,人站在墙根儿里能露出半个身子,往往是人没到声音先是入了堂屋了。更没有像样的红大门,甚至有的连门都没有,就只是在墙上像是豁出个口子,供人来回的出入。
梨树是没熬过几个春夏秋就被驻心虫给终结了一生。或许是刚开始时没在意,穷人得病以为扛一阵儿就好了,从此就又是生龙活虎。却不曾想那棵梨树一扛就再没柳暗花明过。我以为的病树前头万木春,谁曾想沉舟侧畔千帆过,唯独不见梨花开过。于是干巴巴的枝干在家门口立了些年头,后来不知怎地就被劈柴而烧了,从此再也没闻到过淡淡的梨香木。
好歹,两棵树还榴有一棵,毕竟梨则离。
夏末秋初石榴树枝繁叶茂的时候,麻雀儿,喜鹊儿,还有爱织花衣的小燕子时常在那儿枝头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像是每天都有说不完的快乐事,或许偶尔有时候也为同伴的离去也沉默过。不管如何,石榴树却是不曾孤单过。吻过风,听过雨,舞过了春夏直到秋。
后来的后来,也不知是过了多久,村东头儿的小学从一数到六(年级是一到六年级),时过境迁里,从六数到一。家门口的石榴却是越结越多。高高的枝头上,碗口大的石榴,笑裂了嘴,红红的石榴籽儿,星罗密布的排成了排,像极了小卖铺里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好吃的食物,哈喇子口水用手兜都兜不住。个子不高,凳子来凑,凳子不够,镰刀来凑。
满嘴的石榴籽儿,像是香甜的梦,一口一口的嚼碎在现实中。
日子就这样在花开叶落的间隙里悄然滑过,殊不知是在夏末还是秋初的日子里,是雷雨还是狂风不休的雨天,还是一个沁人心脾的秋日暖阳里。那棵石榴树病了,整个的树枝垮了下来,叶上浸润着泥,无精打采的,像是一夜里输掉了所有的运气,不再能东山再起。
一个人最难的时候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当希望摆在你面前,触手可及,啪的一声破碎掉时,让你来不及绝望,就被淹没掉一整个的幻象里。
只是,梨树走了,石榴树还在;石榴树走了,麻雀还在;小燕子飞走了,喜鹊却还不来。
少年亦非是那个少年。懵懵懂懂的日子里却也步入大学校园。日子说长不长,说短却也不短。有时候你越是感叹时光的冗长,却越是上了时光的当,悔不当前。只是留给你回忆的空间却越来越小,最后只能紧缩到方寸大小的盒之中。留待后人指指点点里勾勒出你一世荒凉里有几个安逸瞬间。
待在校园里的最后一个暑假期,闲散时光里总爱寻寻觅觅。寻的一间教室,好久没有摊书提笔,你自以为的认真学习其实只不过是在别人眼中的东施效颦而已。自己却深陷其中,当局者迷而已。要不然,人生何来柴米油盐里添油加醋的痕迹。
恰巧,窗外有一棵,两棵,棵石榴树。独木不成林。犹记得家中那两棵梨树和石榴树,装饰了我一整个童年里对林立成群的想象。
窗外的石榴树,枝条纤细,整个树干不及柔弱小臂。挂的石榴倒是不少,个头儿却也不及半个拳头般大。拳头般大的就算是称的上整个石榴树上的王了。
有时候,不知何时在何地,遇到某人或某事,感觉相识却又熟悉。睡眼惺忪里不小心间恍惚了眼角的迷离。错以为自己坐上了时光机,穿越到了过去,却不曾想半步都没踏出自己画的牢域,封锁住了自己。
石榴多半,大抵是没熟的。红红的外壳下包裹着青白色的籽粒,无味可嘬。犹如你干巴巴的噘着嘴嚼巴不出岁月的痕迹。却有不少人,有的是单枪匹马的搁哪儿抢,有的是三五成群的搁哪儿薅。反正是趋之若鹜,是不亦乐乎。有道是雁过留名,人过却只是留下一地的树叶而已。
时光像是张开了口袋,不管是急急忙忙,还是慢慢悠悠,就等着人们往里跳,有的人惯性的随着前面的人往里跳,有的人是临跳前还不忘记骂句娘。格老子的。
你以为你能凭着一己之力堵住一整个青春的缺口,自以为是的力大无比无所不及,其实它会自动过滤掉关于你青春里的不着边际,继续的沉沦下去。
窗外的那棵石榴树,还会继续驻立在那里。来年花开里藏着令人娇羞的笑意,只是,关于青春里的那些风生水起,它是否还会记忆起。
或许早已忘记,时光湮没下的回忆里。
犹记得,
吻过风,听过雨,舞过春夏直到秋的那棵石榴树。
来年入秋里,依然继续。
乐此不疲的收拾着满目疮痍的残局。
不知不觉,却早已泪眼婆娑。望一眼窗外那棵石榴树,拱手一生里,记忆最深的却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不完美,凝聚成为我们心中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