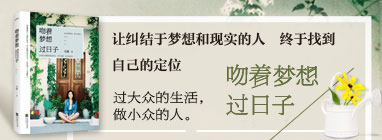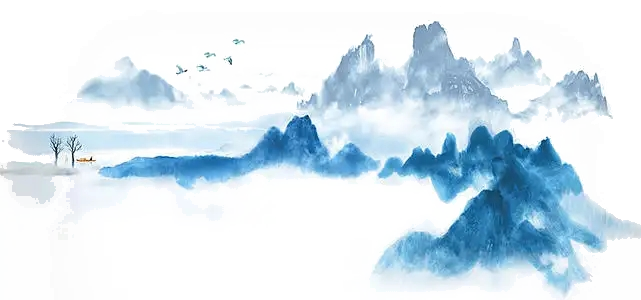文/香港女作家西西
主播/简洁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是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的。但我和夏之间的感情发展到今日这样的地步,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想,我所以能陷入目前的不可自拔的处境,完全是由于命运对我作了残酷的摆布,对于命运;我是没有办法反击的。
听人家说,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只要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看他即使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微笑,你也会忽然地感到魂飞魄散。
对于夏,我的感觉正是这样。所以,当夏问我“你喜欢我吗”的时候.我就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我的感情。我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我的举止和言语,都会使我永远成为别人的笑柄。和夏一起坐在咖啡室里的时候,我看来是那么地快乐,但我的心中充满隐忧,我其实是极度地不快乐的,因为我已经预知命运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而那完全是由于我的过错。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应该答应和夏一起到远方去探望一位久别的同学,而后来,我又没有拒绝和他一起经常看电影。
对于这些事情,后悔已经太迟了,而事实上,后悔或者不后悔,分别也变得不太重要。此刻我坐在咖啡室的一角等夏,我答应了带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去参观。而一切又将在那个时刻结束。
当我和夏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很久了,所以当夏问我是在做事了吗?我就说我已经出外工作许多年了。
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问。
替人化妆。
我说
啊,是化妆。
他说。
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
他说。
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女子化妆的人,他喜欢朴素的脸容。他所以注意到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化妆,我想,并不是由于我对他的询问提出了答案而引起了联想,而是由于我的脸比一般的人都显得苍白、我的手也是这样。我的双手和我的脸都比一般人要显得苍白。这是我的工作造成的后果。我知道当我把我的职业说出来的时候,夏就像我曾经有过其他的每一个朋友一般直接地误解了我的意思。
在他的想象中,我的工作是一种为了美化一般女子的容貌的工作,譬如,在婚礼的节日上,为将出嫁的新娘端丽她们的颜面,所以,当我说我的工作并没有假期,即使是星期天也常常是忙碌的,他就更加信以为真了。
星期天或者假日总有那么多的新娘。但我的工作并非为新娘化妆。我的工作是为那些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人作最后的修饰。使他们在将离人世的最后,刻显得心平气和与温柔。在过往的日子里,我也曾经把我的职业对我的朋友提及,当他们稍有误会时我立刻加以更正辩析.让他们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我的诚实使我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是我使他们害怕了,仿佛坐在他们对面喝着咖啡的我竟也是他们心目中恐惧的幽灵了。这我是不怪他们的。对于生命中不可知的神秘面我们天生就有原始的胆怯。我没有在对夏的问题提出答案时加以解释,一则是由于我怕他也会因此惊俱,我是不可以再由于自己的奇异职业而使我周遭的朋友感到不安,这样我将更不能原谅我自己;其次,是由于我原是一个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意思的人,长期以来,我习惯了保持沉默。
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
他说。
当夏这样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路上不祥的预兆了。但那时候.夏是那么地快乐,因为我是一个不为自己化妆的女子而快乐,但我的心中充满了忧愁。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将是为我的脸化妆的一个人,会是怡芬姑母吗?我和怡芬姑母一样,我们共同的愿望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不要为我们自己至爱的亲人化妆。我不知道在不祥的预兆跃升之后,我为什么继续和夏一起常常漫游,也许,我毕竟是一个人,我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而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命运所指引我走的道路上去;其实,对于我的种种行为,我自己也无法作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人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人的行为有许多都是令人莫名其妙的。
我可以参观你的工作吗?
夏问。
应该没有问题。
我说。
她们会介意吗?
他问。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介意的。
我说。
夏所以说要参观一下我的工作,是因为那个星期日的早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去工作,而他在这个日子里并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他说他愿意陪我上我工作的地方,既然去了,为什么不留下来看看呢。他说他想看那些新娘和送嫁的女子们热闹的情形,也想看看我怎样把她们打扮得花容月貌,或者化丑为妍。
我毫不考虑地答应了。
我知道命运已经把我带向起步的白线前面,而这注定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在一间小小的咖啡室里等夏来。然后我们一起到我工作的地方去。
到了那个地方,一切就会明白了。
夏就会知道他一直以为是我为他而洒的香水,其实不过是附在我身体上的防腐剂的气味罢了;他也会知道,我常常穿素白的衣服,并不是因为这是我特意追求纯洁的表征,而是为了方便出入我工作的那个地方。附在我身上的一种奇异的药水气味.已经在我的躯体上蚀骨了,我曾经用过种种的方法把它们洗涤清洁都无法把它们驱除,直到后来,我终于放弃了我的努力,我甚至不再闻得那股特殊的气息,夏却是一无所知的,他曾经对我说:你用的是多么奇特的一种香水。但一切不久就会水落石出。
我一直是一名能够修理一个典雅发型的技师,我也是个能束一个美丽出色的领结的巧手,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看我的双手,它们曾为多少沉默不语的人修剪过发髭,又为多少严肃庄重的颈项整理过他们的领结。
这双手,夏能容忍我为他理发吗?能容忍我为他细心打一条领带吗?这样的一双手,本来是温暖的,但在人们的眼中已经变成冰冷,这样的一双手,本来是可以怀抱新生的婴儿的,但在人们的眼中已经成为安抚骷髅的白骨了。
怡芬姑母把她的技艺传授给我,也许有甚多的理由,人们从她平日的言谈中可以探测得清清楚楚。不错,像这般的一种技艺,是一生一世也不怕失业的一种技艺,而且收入甚丰,像我这样一个读书不多,知识程度低的女子,有什么能力到这个狼吞虎咽、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去和别的人竞争呢。
怡芬姑母把她的毕生绝学传授给我,完全是因为我是她的亲侄女儿的缘故。她工作的时候,从来不让任何一个人参观,直到她正式的收我为她的门徒,才让我追随她的左右,跟着她一点一点地学习,即便独自对着赤裸而冰冷的尸体也不觉得害怕。甚至那些碎裂得四分五散的部分、爆裂的头颅,我已学会了把它们拼凑缝接起来,仿佛这不过是在制作一件戏服。我从小失去父母,由怡芬姑母把我抚养长大。
奇怪的是,我终于渐渐地变得愈来愈像我的姑母,甚至是她的沉默寡言,她的苍白的手睑,她步行时慢吞吞的姿态,我都愈来愈像她。有时候我不禁感到怀疑,我究竟是不是我自己,我或者竟是另外的一个怡芬姑母,我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我就是怡芬姑母的一个延续。
从今以后,你将不愁衣食了。
怡芬姑母说。
你也不必像别的女子那般,要靠别的人来养活你了。
她说。
怡芬姑母这样说,我其实是不明白她的意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跟着她学会了这一种技能,我可以不愁衣食,不必像别的女子要靠别的人来养活,难道世界上就没有别的行业可以令我也不愁衣食,不必靠别的人来养活么。但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必定不能和别的女子竞争的,所以,怡芬姑母才特别传授了她的特技给我。她完全是为了我好,事实上,像我们这样的工作,整个城市的人,谁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呢,不管是什么人,穷的还是富的。大官还是乞丐,只要命运的手把他们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是他们最终的安慰,我们会使他们的容颜显得心平气和,使他们显得无比的温柔。
我和怡芬姑母都各自有各自的愿望,除了自己的愿望以外。我们尚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必为我们至爱的亲人化妆。
所以,上一个星期之内,我是那么地悲哀,我隐隐约约知道有一件凄凉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件事,却是发生在我年轻兄弟的身上。据我所知,我年轻的兄弟结识了一位声色、性情令人赞美的女子,而且是才貌双全的,他们彼此是那么地快乐,我想,这真是一件幸福的大喜事,然而快乐毕竟是过得太快一点了,我不久就知道那可爱的女子不明不白地和一个她并不相爱的人结了婚。为什么两个本来相爱的人不能结婚,却被逼要苦苦相思一生呢?
我年轻的兄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他曾经这么说:我不要活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难道我竟要为我年轻的兄弟化妆吗?
我不要活了。
我年轻的兄弟说。
我完全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那样,我年轻的兄弟也不明白。如果她说;我不喜欢你了,那我年轻的兄弟无话可说的。但两个人明明相爱,既不是为了报恩,又不是经济上的困难,而在这么文明的现代社会,还有被父母逼了出嫁的女子吗?
长长的一生为什么就对命运低头了呢?
唉,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都不必为我们至爱的亲人化妆。
不过谁能说得准呢,怡芬姑母在正式收我为徒,传授我绝技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你必须遵从我一件事情,我才能收你为门徒。我不知道为什么怡芬姑母那么郑重其事,她严肃地对我说:当我躺下,你必须亲自为我化妆,不要让任何陌生人接触我的躯体。
我觉得这样的事并不困难,只是奇怪怡芬姑母的执着,譬如我,当我躺下,我的躯体与我,还有什么相干呢?但那是怡芬姑母唯一的私自的愿望,我必会帮助她完成,只要我能活到那个适当的时刻和年月。
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上,我和怡芬姑母一样,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宏大的愿望,怡芬姑母希望我是她的化妆师,而我,我只希望凭我的技艺,能够创造一个“最安详的死者”出来,他将比所有的死者更温柔,更心平气和,仿佛死亡真的是最佳的安息。
其实,即使我果然成功了,也不过是我在人世上无聊时借以杀死时间的一种游戏罢了。世界上的一切岂不毫无意义。我的努力其实是一场徒劳。
如果我创造了“最安详的死者”,我难道希望得到奖赏?死者是一无所知的,死者的家属也不会知道我在死者身上所花的心力,我又不会举行展览会!让公众进来参观分辨化妆师的优劣与创新,更加没有人会为死者的化妆作不同的评述、比较、研究和开讨论会,这只是斗室中我个人的一项游戏而已,但我为什么又作出了我的愿望呢?
这大概就是支持我继续我的工作的一种动力了。因为我的工作是寂寞而孤独的,既没有对手,也没有观众,当然也没有掌声。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只听见我自已低低的呼吸,满室躺着男男女女,只有我自已独自低低的呼吸,我甚至可以感到我的心在哀愁或者叹息,当别人的心都停止了悲鸣的时候,我的心就更加响亮了。
昨天,我想为一双为情自杀的年轻人化妆,当我凝视那个沉睡了的男孩的脸时,我忽然觉得这正是我创造“最安详的死者”的对象。
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合上了嘴唇,他的左额上有一个淡淡的疤痕,他那样地睡着,仿佛真的不过是在安详睡觉。
这么多年,我所化妆过的脸何止千万,许多都是愁眉苦脸的,大部分十分狰狞,对于这些面谱,我一 一为他们作了最适当的修正,该缝补的缝补,该掩饰的掩饰,使他们变得无限的温柔。
但我昨天遇见的男孩,他的容颜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难道说他的自杀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我不相信这种表面的姿态,我觉得他的行为是一种极端懦弱的行为,一个没有勇气向命运反击的人应该是我不屑一顾的,我不但打消了把他创造为一个“最安详的死者”的念头,同时拒绝为他化妆,我把他和那个和他一起愚蠢地认命的女孩,一起移交给怡芬姑母,让她去为他们因喝剧烈的毒液而烫烧的面颊细细地粉饰。
没有人不知道怡芬姑母的往事,因为有些人曾经是现场的目击者。
那时候怡芬姑母年轻,喜欢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并且和躺在她前面的死者说话,仿佛他们都是她的朋友。至于怡芬姑母变得沉默寡言,那就是后来的事了。怡芬姑母习惯把她心里的一切话都讲给她沉睡了的朋友们听,她从来不写日记,她的话就是她每天的日记,沉睡在她前面的那些人都是人类中最优秀的听众,他们可以长时间地听她娓娓细说,而且,又是第一等的保密者。
怡芬姑母会告诉他们她如何结识一个男子,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所有的恋人们在一起那样地快乐,偶然中间也不乏遥远而断续的、时阴时晴的日子。那时候,怡芬姑母每星期一次上一间美容学校学化妆术,风雨不改,经年不辍,她几乎把所有老师的技艺都学齐了,甚至当学校方面告诉她,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学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要老师们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技术可以传给她;她对化妆的兴趣如此浓厚,几乎是天生的因素,以致她的朋友都以为她将来必是要开什么大规模的美容院。
但她没有,她只把学问贡献在沉睡在她前面的人的躯体上。而这样的事情,她年轻的恋人是不知道的,他一直以为爱美是女孩天性,她不过是比较喜好脂粉罢了。直到这么的一天,她带他到她工作的地方去看看,指着躺在一边的死者,告诉他,这是一种非常孤独而寂寞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并没有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一切的妒忌、仇恨和名利的争执都已不存在.当他们落入阴暗之中,他们将一个个变得心平气和而温柔。
他是那么的惊恐,他从来没想象她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从事这样的一种职业,他曾经爱她,愿意为她做任何事,他起过誓,说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弃她,他们必定白头偕老,他们的爱情至死不渝。不过,在一群不会说话,没有能力呼吸的死者的面前,他的勇气与胆量竟完全消失了,他失声大叫,掉头拔脚而逃,推开了所有的门,一路上有许多人看见他失魂落魄地奔跑。以后,怡芬姑母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人们只听见她独自在一间斗室里,对她沉默的朋友们说:他不是说爱我的么,他不是说他不会离弃我的吗?而他为什么忽然这么惊恐呢。后来,怡芬姑母就变得逐渐沉默寡言起来,或者,她要说的话已经说尽,或者,她不必再说,她沉默的朋友都知道关于她的故事,有些话的确是不必多说的。
怡芬姑母在开始把她的绝技传授给我的时候,也对我讲过她的往事,她选择了我,而没有选择我年轻的兄弟,虽然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却是,我并非一个胆怯的人。
你害怕吗?
她问。
我并不害怕。
我说。
你胆怯吗?
她问。
我并不胆怯。
我说。
是因为我并不害怕。所以怡芬姑母选择了我作她的继承人。她有一个预感,我的命运和她的命运相同。至于我们怎么会变得愈来愈相像,这是我们都无法解释的事情,而开始的原因却是由于我们都不害怕。我们毫不畏惧。当时怡芬姑母把她的往事告诉我的时候,她说,但我总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必定有像我们一般,并不畏惧的人。那时候,怡芬姑母还没有到达完全沉默寡言的程度,她让我站在她的身边,看她怎样为一张倔强的嘴唇涂上红色,又为一只久睁的眼睛轻轻抚摸,请他安息。那时候,她仍断断续续地对她的一群沉睡了的朋友说话:而你,你为什么害怕了呢。为什么在恋爱中的人却对爱那么没有信心,在爱里竟没有勇气呢。在怡芬姑母的沉睡的朋友中,也不乏胆怯而懦弱的家伙,他们则更加沉默了,怡芬姑母很知道她的朋友们的一些故事,她有时候一面为一个额上垂着刘海的女子敷粉一面告诉我:唉唉,这是一个何等懦弱的女子呀,只为了要做一个名义上美丽的孝顺女儿,竟把她心爱的人舍弃了。怡芬姑母知道这边的一个女子是为了报恩,那边的女子是为了认命,都把自己无助地交在命运的手里,仿佛他们并不是一个活生生有感情有思想的人,而是一件件商品。 这真是可怕的工作呀。
我的朋友说。
是为死的人化妆吗,我的天呀。
我的朋友说。
我并不害怕,是我的朋友害怕,他们因为我的眼睛常常凝视死者的眼睛而不喜欢我的眼睛,他们又因为我的手常常抚摸死者的手而不喜欢我的手。
起先他只是不喜欢,渐渐地他们简直就是害伯了,而且,他们起先不喜欢和感到害怕的只是我的眼睛和我的手,但到了后来,他们不喜欢和感到害怕的已经蔓延到我的整体,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从我身边离去。仿佛动物看见烈火,田农骤遇飞蝗。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害怕呢,在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做这样的工作,难道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称职?
但我渐渐就安于我的现状了;对于我的孤独,我也习惯了。总有那么多的人,追寻一些温暖甜蜜的工作,他们喜欢的永远是星星与花朵。
但在星星与花朵之中,怎样才显得出一个人坚定的步伐呢。我如今几乎没有朋友了,他们从我的手感觉到另一个深邃的国度与冰冷,他们从我的眼睛看见无数沉默浮游的精灵,于是,他们感到害伯了。即使我的手是温暖的,我的眼睛是会流泪的,我的心是热的,他们并不回顾。
我也开始像我的怡芬姑母那样。只剩下沉睡在我的面前的死者成为我的朋友了。奇怪我在静寂的时候居然会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明天早上,我会带一个叫做夏的人到这里来探访你们。夏问过:你们会介意吗?我说,你们并不介意,你们是真的不介意吧。到了明天,夏就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想,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是怎样的。因为我的命运已经和怡芬姑母的命运重叠为一了。我想,我当会看到夏踏进这个地方时的魂飞魄散的样子,唉,我们竟以不同的方式彼此令彼此魂飞魄散。
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惊恐。我从种种的预兆中已经知道结局的场面。夏说: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是的,我的脸是那样朴素,一张朴素的脸并没有力量令一个人对一切变得无所畏惧。 我曾经想过转换一种职业,难道我不能像别的女子那样做一些别的工作吗?我已经没有可能当教师、护士,或者写字楼的秘书或文员,但我难道不能到商店去当售货员,到面包店去卖面包,甚至是当一名清洁女佣?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只要求一日的餐宿,难道无处可以容身?说实在的,凭我的一手技艺,我真的可以当那些新娘的美容师,但我不敢想象,当我为一张嘴唇涂上唇膏时,嘴唇忽然裂开而显出一个微笑时,我会怎么想,太多的记忆使我不能从事这一项与我非常相称的职业。
只是,如果我转换了一份工作,我的苍白的手脸会改变他们的颜色吗,我的满身蚀骨的防腐剂的药味会完全彻底消失吗?
那时,对于夏,我又该把我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绝对地隐瞒吗?对一个我们至亲的人隐瞒过往的事,是不忠诚的,世界上仍有无数的女子,千方百计的掩饰她们愧失了的贞节和虚长了的年岁。
这都是我所鄙视的人物。
我必定会对夏说,我长时期的工作,一直是在为一些沉睡了的死者化妆。而他必须知道、认识,我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所以,我身上并没有奇异的香水气味,而是防腐剂的药水味;我常常穿白色的衣裳也并非由于我刻意追求纯洁的形象,而是我必须如此才能方便出入我工作的地方。
但这些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些水珠罢了,当夏知道我的手长时期触抚那些沉睡的死者,他还会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跃过急流的涧溪吗?
他会让我为他修剪头发,为他打一个领结吗?
他会容忍我的视线凝定在他的脸上吗?
他会毫不恐惧地在我的面前躺下来吗?
我想他会害伯,他会非常害怕,他就像我的那些朋友。起先是惊讶,然后是不喜欢,结果就是害怕而掉转脸去。
怡芬姑母说:如果是由于爱,那还有什么畏惧的呢.但我知道,许多人的所谓爱,表面上是非常地刚强、坚韧,事实上却异常的脆弱、柔萎;吹了气的勇气,不过是一层糖衣。
怡芬姑母说:也许夏不是一个胆怯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对我的职业不作进一步解释的缘故,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完全是一个不擅于表达自己思想的人,我可能说得不好,可能选错了环境,气候、时间和温度,这都会把我想表达的意思改变.我不对夏解释我的工作并非是为新娘添妆,其实也正是对他的一种考验,我要观察他看见我工作对象时的反应,如果他害怕,那么他就是害怕了。
如果他拔脚而逃,让我告诉我那些沉睡的朋友;其实一切就从来没有发生。
我可以参观一下你工作的情形吗?
他问。
应该没有问题。
我说。
所以,如今我坐在咖啡室的一个角落等夏来。我曾经在这个时刻仔细地思想,也许我这样对夏是不公平的,如果他对我所从事的行业感到害怕,而这又有什么过错呢?为什么他要特别勇敢,为什么一个人对死者的恐惧竟要和爱情上的胆怯有关,那可能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已经亡故了,都是由怡芬姑母把我扶养长大的,我,以及我年轻的兄弟,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我对父母的身世和他们的往事所知甚少,一切我稍后知悉的事都是怡芬姑母告诉我的,我记得她说过,我的父亲正是从事为死者化妆的一个人,他后来娶了我的母亲。当他打算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曾经问她:你害怕吗?但我母亲说;并不害怕。
我想,我所以也不害怕.是因为我像我的母亲,我身体内的血液原是她的血液。怡芬姑母说,我母亲在她的记忆中是永生的,因为她这么说过:因为爱,所以并不害怕.也许是这样,我不记得我母亲的模样和声音。
但她隐隐约约地在我的记忆中也是永生的。
可是我想,如果我母亲说了因为爱而不害怕的话,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没有理由要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如此。或者,我还应该责备自己从小接受了这样的命运。从事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职业,世界上哪一个男子不喜爱那些温柔、暖和、甜言的女子呢?而那些女子也该从事一些亲切、婉约、典雅的工作。
但我的工作是冰冷而阴森、暮气沉沉的,我想我个人早已也染上了那样的一种雾霭,那么,为什么一个明亮如太阳似的男子要娶这样一个郁暗的女子呢,当他躺在她的身边,难道不会想起这是一个经常和尸体相处的一个人,而她的双手,触及他的肌肤时,会不会令他想起,这竟是一双长期轻抚死者的手呢。唉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原是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的。我想一切的过失皆自我而起,我何不离开这里,回到我工作的地方去,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叫做夏,而他也将忘记曾经认识过一个女子。是一名为新娘添妆的美容师。
不过一切又仿佛太迟了,我看见夏,透过玻璃,从马路的对面走过来。他手里抱着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一束花。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过生日吗。我看着夏从咖啡室的门口进来。发现我坐在这边幽暗的角落里.外面的阳光非常灿烂,他把阳光带进来,因为他的白色的衬衫反映了那种光亮。他像他的名字,永远是夏天。
喂,星期日快乐。
他说。
这些花都是送给你的。
他说。
他的确是快乐的,于是他坐下来喝咖啡。我们有过那么多快乐的日子。但快乐又是什么呢,快乐总是过得很快的。我的心是那么地忧愁。从这里走过去,不过是三百步路的光景,我们就可以到达我工作的地方。然后,就像许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一个失魂落魄的男子从那扇大门里飞跑出来,所有好奇的眼睛都跟踪着他,直至他完全消失。怡芬姑母说: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仍有真正具备勇气而不畏惧的人。
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假设,当夏从对面的马路走过来的时候,手抱一束巨大的花朵,我又已经知道.因为这正是不祥的预兆。
唉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是不宜和任何人恋爱的,或者,我该对我的那些沉睡了的朋友说:我们其实不都是一样的吗?几十年不过匆匆一瞥,无论是为了什么因由,原是谁也不必为谁而魂飞魄散的。夏带进咖啡室来的一束巨大的花朵,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他是快乐的,而我心忧伤。
他是不知道的,在我们这个行业之中,花朵,就是诀别的意思。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文/香港女作家西西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是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的。但我和夏之间的感情发展到今日这样的地步,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想,我所以能陷入目前的不可自拔的处境,完全是由于命运对我作了残酷的摆布,对于命运;我是没有办法反击的。
听人家说,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只要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看他即使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微笑,你也会忽然地感到魂飞魄散。
对于夏,我的感觉正是这样。所以,当夏问我“你喜欢我吗”的时候.我就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我的感情。我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我的举止和言语,都会使我永远成为别人的笑柄。和夏一起坐在咖啡室里的时候,我看来是那么地快乐,但我的心中充满隐忧,我其实是极度地不快乐的,因为我已经预知命运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而那完全是由于我的过错。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应该答应和夏一起到远方去探望一位久别的同学,而后来,我又没有拒绝和他一起经常看电影。
对于这些事情,后悔已经太迟了,而事实上,后悔或者不后悔,分别也变得不太重要。此刻我坐在咖啡室的一角等夏,我答应了带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去参观。而一切又将在那个时刻结束。
当我和夏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很久了,所以当夏问我是在做事了吗?我就说我已经出外工作许多年了。
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问。
替人化妆。
我说
啊,是化妆。
他说。
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
他说。
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女子化妆的人,他喜欢朴素的脸容。他所以注意到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化妆,我想,并不是由于我对他的询问提出了答案而引起了联想,而是由于我的脸比一般的人都显得苍白、我的手也是这样。我的双手和我的脸都比一般人要显得苍白。这是我的工作造成的后果。我知道当我把我的职业说出来的时候,夏就像我曾经有过其他的每一个朋友一般直接地误解了我的意思。
在他的想象中,我的工作是一种为了美化一般女子的容貌的工作,譬如,在婚礼的节日上,为将出嫁的新娘端丽她们的颜面,所以,当我说我的工作并没有假期,即使是星期天也常常是忙碌的,他就更加信以为真了。
星期天或者假日总有那么多的新娘。但我的工作并非为新娘化妆。我的工作是为那些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人作最后的修饰。使他们在将离人世的最后,刻显得心平气和与温柔。在过往的日子里,我也曾经把我的职业对我的朋友提及,当他们稍有误会时我立刻加以更正辩析.让他们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我的诚实使我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是我使他们害怕了,仿佛坐在他们对面喝着咖啡的我竟也是他们心目中恐惧的幽灵了。这我是不怪他们的。对于生命中不可知的神秘面我们天生就有原始的胆怯。我没有在对夏的问题提出答案时加以解释,一则是由于我怕他也会因此惊俱,我是不可以再由于自己的奇异职业而使我周遭的朋友感到不安,这样我将更不能原谅我自己;其次,是由于我原是一个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意思的人,长期以来,我习惯了保持沉默。
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
他说。
当夏这样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路上不祥的预兆了。但那时候.夏是那么地快乐,因为我是一个不为自己化妆的女子而快乐,但我的心中充满了忧愁。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将是为我的脸化妆的一个人,会是怡芬姑母吗?我和怡芬姑母一样,我们共同的愿望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不要为我们自己至爱的亲人化妆。我不知道在不祥的预兆跃升之后,我为什么继续和夏一起常常漫游,也许,我毕竟是一个人,我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而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命运所指引我走的道路上去;其实,对于我的种种行为,我自己也无法作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人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人的行为有许多都是令人莫名其妙的。
我可以参观你的工作吗?
夏问。
应该没有问题。
我说。
她们会介意吗?
他问。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介意的。
我说。
夏所以说要参观一下我的工作,是因为那个星期日的早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去工作,而他在这个日子里并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他说他愿意陪我上我工作的地方,既然去了,为什么不留下来看看呢。他说他想看那些新娘和送嫁的女子们热闹的情形,也想看看我怎样把她们打扮得花容月貌,或者化丑为妍。
我毫不考虑地答应了。
我知道命运已经把我带向起步的白线前面,而这注定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在一间小小的咖啡室里等夏来。然后我们一起到我工作的地方去。
到了那个地方,一切就会明白了。
夏就会知道他一直以为是我为他而洒的香水,其实不过是附在我身体上的防腐剂的气味罢了;他也会知道,我常常穿素白的衣服,并不是因为这是我特意追求纯洁的表征,而是为了方便出入我工作的那个地方。附在我身上的一种奇异的药水气味.已经在我的躯体上蚀骨了,我曾经用过种种的方法把它们洗涤清洁都无法把它们驱除,直到后来,我终于放弃了我的努力,我甚至不再闻得那股特殊的气息,夏却是一无所知的,他曾经对我说:你用的是多么奇特的一种香水。但一切不久就会水落石出。
我一直是一名能够修理一个典雅发型的技师,我也是个能束一个美丽出色的领结的巧手,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看我的双手,它们曾为多少沉默不语的人修剪过发髭,又为多少严肃庄重的颈项整理过他们的领结。
这双手,夏能容忍我为他理发吗?能容忍我为他细心打一条领带吗?这样的一双手,本来是温暖的,但在人们的眼中已经变成冰冷,这样的一双手,本来是可以怀抱新生的婴儿的,但在人们的眼中已经成为安抚骷髅的白骨了。
怡芬姑母把她的技艺传授给我,也许有甚多的理由,人们从她平日的言谈中可以探测得清清楚楚。不错,像这般的一种技艺,是一生一世也不怕失业的一种技艺,而且收入甚丰,像我这样一个读书不多,知识程度低的女子,有什么能力到这个狼吞虎咽、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去和别的人竞争呢。
怡芬姑母把她的毕生绝学传授给我,完全是因为我是她的亲侄女儿的缘故。她工作的时候,从来不让任何一个人参观,直到她正式的收我为她的门徒,才让我追随她的左右,跟着她一点一点地学习,即便独自对着赤裸而冰冷的尸体也不觉得害怕。甚至那些碎裂得四分五散的部分、爆裂的头颅,我已学会了把它们拼凑缝接起来,仿佛这不过是在制作一件戏服。我从小失去父母,由怡芬姑母把我抚养长大。
奇怪的是,我终于渐渐地变得愈来愈像我的姑母,甚至是她的沉默寡言,她的苍白的手睑,她步行时慢吞吞的姿态,我都愈来愈像她。有时候我不禁感到怀疑,我究竟是不是我自己,我或者竟是另外的一个怡芬姑母,我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我就是怡芬姑母的一个延续。
从今以后,你将不愁衣食了。
怡芬姑母说。
你也不必像别的女子那般,要靠别的人来养活你了。
她说。
怡芬姑母这样说,我其实是不明白她的意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跟着她学会了这一种技能,我可以不愁衣食,不必像别的女子要靠别的人来养活,难道世界上就没有别的行业可以令我也不愁衣食,不必靠别的人来养活么。但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必定不能和别的女子竞争的,所以,怡芬姑母才特别传授了她的特技给我。她完全是为了我好,事实上,像我们这样的工作,整个城市的人,谁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呢,不管是什么人,穷的还是富的。大官还是乞丐,只要命运的手把他们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是他们最终的安慰,我们会使他们的容颜显得心平气和,使他们显得无比的温柔。
我和怡芬姑母都各自有各自的愿望,除了自己的愿望以外。我们尚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必为我们至爱的亲人化妆。
所以,上一个星期之内,我是那么地悲哀,我隐隐约约知道有一件凄凉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件事,却是发生在我年轻兄弟的身上。据我所知,我年轻的兄弟结识了一位声色、性情令人赞美的女子,而且是才貌双全的,他们彼此是那么地快乐,我想,这真是一件幸福的大喜事,然而快乐毕竟是过得太快一点了,我不久就知道那可爱的女子不明不白地和一个她并不相爱的人结了婚。为什么两个本来相爱的人不能结婚,却被逼要苦苦相思一生呢?
我年轻的兄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他曾经这么说:我不要活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难道我竟要为我年轻的兄弟化妆吗?
我不要活了。
我年轻的兄弟说。
我完全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那样,我年轻的兄弟也不明白。如果她说;我不喜欢你了,那我年轻的兄弟无话可说的。但两个人明明相爱,既不是为了报恩,又不是经济上的困难,而在这么文明的现代社会,还有被父母逼了出嫁的女子吗?
长长的一生为什么就对命运低头了呢?
唉,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都不必为我们至爱的亲人化妆。
不过谁能说得准呢,怡芬姑母在正式收我为徒,传授我绝技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你必须遵从我一件事情,我才能收你为门徒。我不知道为什么怡芬姑母那么郑重其事,她严肃地对我说:当我躺下,你必须亲自为我化妆,不要让任何陌生人接触我的躯体。
我觉得这样的事并不困难,只是奇怪怡芬姑母的执着,譬如我,当我躺下,我的躯体与我,还有什么相干呢?但那是怡芬姑母唯一的私自的愿望,我必会帮助她完成,只要我能活到那个适当的时刻和年月。
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上,我和怡芬姑母一样,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宏大的愿望,怡芬姑母希望我是她的化妆师,而我,我只希望凭我的技艺,能够创造一个“最安详的死者”出来,他将比所有的死者更温柔,更心平气和,仿佛死亡真的是最佳的安息。
其实,即使我果然成功了,也不过是我在人世上无聊时借以杀死时间的一种游戏罢了。世界上的一切岂不毫无意义。我的努力其实是一场徒劳。
如果我创造了“最安详的死者”,我难道希望得到奖赏?死者是一无所知的,死者的家属也不会知道我在死者身上所花的心力,我又不会举行展览会!让公众进来参观分辨化妆师的优劣与创新,更加没有人会为死者的化妆作不同的评述、比较、研究和开讨论会,这只是斗室中我个人的一项游戏而已,但我为什么又作出了我的愿望呢?
这大概就是支持我继续我的工作的一种动力了。因为我的工作是寂寞而孤独的,既没有对手,也没有观众,当然也没有掌声。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只听见我自已低低的呼吸,满室躺着男男女女,只有我自已独自低低的呼吸,我甚至可以感到我的心在哀愁或者叹息,当别人的心都停止了悲鸣的时候,我的心就更加响亮了。
昨天,我想为一双为情自杀的年轻人化妆,当我凝视那个沉睡了的男孩的脸时,我忽然觉得这正是我创造“最安详的死者”的对象。
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合上了嘴唇,他的左额上有一个淡淡的疤痕,他那样地睡着,仿佛真的不过是在安详睡觉。
这么多年,我所化妆过的脸何止千万,许多都是愁眉苦脸的,大部分十分狰狞,对于这些面谱,我一 一为他们作了最适当的修正,该缝补的缝补,该掩饰的掩饰,使他们变得无限的温柔。
但我昨天遇见的男孩,他的容颜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难道说他的自杀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我不相信这种表面的姿态,我觉得他的行为是一种极端懦弱的行为,一个没有勇气向命运反击的人应该是我不屑一顾的,我不但打消了把他创造为一个“最安详的死者”的念头,同时拒绝为他化妆,我把他和那个和他一起愚蠢地认命的女孩,一起移交给怡芬姑母,让她去为他们因喝剧烈的毒液而烫烧的面颊细细地粉饰。
没有人不知道怡芬姑母的往事,因为有些人曾经是现场的目击者。
那时候怡芬姑母年轻,喜欢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并且和躺在她前面的死者说话,仿佛他们都是她的朋友。至于怡芬姑母变得沉默寡言,那就是后来的事了。怡芬姑母习惯把她心里的一切话都讲给她沉睡了的朋友们听,她从来不写日记,她的话就是她每天的日记,沉睡在她前面的那些人都是人类中最优秀的听众,他们可以长时间地听她娓娓细说,而且,又是第一等的保密者。
怡芬姑母会告诉他们她如何结识一个男子,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所有的恋人们在一起那样地快乐,偶然中间也不乏遥远而断续的、时阴时晴的日子。那时候,怡芬姑母每星期一次上一间美容学校学化妆术,风雨不改,经年不辍,她几乎把所有老师的技艺都学齐了,甚至当学校方面告诉她,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学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要老师们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技术可以传给她;她对化妆的兴趣如此浓厚,几乎是天生的因素,以致她的朋友都以为她将来必是要开什么大规模的美容院。
但她没有,她只把学问贡献在沉睡在她前面的人的躯体上。而这样的事情,她年轻的恋人是不知道的,他一直以为爱美是女孩天性,她不过是比较喜好脂粉罢了。直到这么的一天,她带他到她工作的地方去看看,指着躺在一边的死者,告诉他,这是一种非常孤独而寂寞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并没有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一切的妒忌、仇恨和名利的争执都已不存在.当他们落入阴暗之中,他们将一个个变得心平气和而温柔。
他是那么的惊恐,他从来没想象她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从事这样的一种职业,他曾经爱她,愿意为她做任何事,他起过誓,说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弃她,他们必定白头偕老,他们的爱情至死不渝。不过,在一群不会说话,没有能力呼吸的死者的面前,他的勇气与胆量竟完全消失了,他失声大叫,掉头拔脚而逃,推开了所有的门,一路上有许多人看见他失魂落魄地奔跑。以后,怡芬姑母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人们只听见她独自在一间斗室里,对她沉默的朋友们说:他不是说爱我的么,他不是说他不会离弃我的吗?而他为什么忽然这么惊恐呢。后来,怡芬姑母就变得逐渐沉默寡言起来,或者,她要说的话已经说尽,或者,她不必再说,她沉默的朋友都知道关于她的故事,有些话的确是不必多说的。
怡芬姑母在开始把她的绝技传授给我的时候,也对我讲过她的往事,她选择了我,而没有选择我年轻的兄弟,虽然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却是,我并非一个胆怯的人。
你害怕吗?
她问。
我并不害怕。
我说。
你胆怯吗?
她问。
我并不胆怯。
我说。
是因为我并不害怕。所以怡芬姑母选择了我作她的继承人。她有一个预感,我的命运和她的命运相同。至于我们怎么会变得愈来愈相像,这是我们都无法解释的事情,而开始的原因却是由于我们都不害怕。我们毫不畏惧。当时怡芬姑母把她的往事告诉我的时候,她说,但我总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必定有像我们一般,并不畏惧的人。那时候,怡芬姑母还没有到达完全沉默寡言的程度,她让我站在她的身边,看她怎样为一张倔强的嘴唇涂上红色,又为一只久睁的眼睛轻轻抚摸,请他安息。那时候,她仍断断续续地对她的一群沉睡了的朋友说话:而你,你为什么害怕了呢。为什么在恋爱中的人却对爱那么没有信心,在爱里竟没有勇气呢。在怡芬姑母的沉睡的朋友中,也不乏胆怯而懦弱的家伙,他们则更加沉默了,怡芬姑母很知道她的朋友们的一些故事,她有时候一面为一个额上垂着刘海的女子敷粉一面告诉我:唉唉,这是一个何等懦弱的女子呀,只为了要做一个名义上美丽的孝顺女儿,竟把她心爱的人舍弃了。怡芬姑母知道这边的一个女子是为了报恩,那边的女子是为了认命,都把自己无助地交在命运的手里,仿佛他们并不是一个活生生有感情有思想的人,而是一件件商品。 这真是可怕的工作呀。
我的朋友说。
是为死的人化妆吗,我的天呀。
我的朋友说。
我并不害怕,是我的朋友害怕,他们因为我的眼睛常常凝视死者的眼睛而不喜欢我的眼睛,他们又因为我的手常常抚摸死者的手而不喜欢我的手。
起先他只是不喜欢,渐渐地他们简直就是害伯了,而且,他们起先不喜欢和感到害怕的只是我的眼睛和我的手,但到了后来,他们不喜欢和感到害怕的已经蔓延到我的整体,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从我身边离去。仿佛动物看见烈火,田农骤遇飞蝗。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害怕呢,在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做这样的工作,难道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称职?
但我渐渐就安于我的现状了;对于我的孤独,我也习惯了。总有那么多的人,追寻一些温暖甜蜜的工作,他们喜欢的永远是星星与花朵。
但在星星与花朵之中,怎样才显得出一个人坚定的步伐呢。我如今几乎没有朋友了,他们从我的手感觉到另一个深邃的国度与冰冷,他们从我的眼睛看见无数沉默浮游的精灵,于是,他们感到害伯了。即使我的手是温暖的,我的眼睛是会流泪的,我的心是热的,他们并不回顾。
我也开始像我的怡芬姑母那样。只剩下沉睡在我的面前的死者成为我的朋友了。奇怪我在静寂的时候居然会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明天早上,我会带一个叫做夏的人到这里来探访你们。夏问过:你们会介意吗?我说,你们并不介意,你们是真的不介意吧。到了明天,夏就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想,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是怎样的。因为我的命运已经和怡芬姑母的命运重叠为一了。我想,我当会看到夏踏进这个地方时的魂飞魄散的样子,唉,我们竟以不同的方式彼此令彼此魂飞魄散。
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惊恐。我从种种的预兆中已经知道结局的场面。夏说: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是的,我的脸是那样朴素,一张朴素的脸并没有力量令一个人对一切变得无所畏惧。 我曾经想过转换一种职业,难道我不能像别的女子那样做一些别的工作吗?我已经没有可能当教师、护士,或者写字楼的秘书或文员,但我难道不能到商店去当售货员,到面包店去卖面包,甚至是当一名清洁女佣?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只要求一日的餐宿,难道无处可以容身?说实在的,凭我的一手技艺,我真的可以当那些新娘的美容师,但我不敢想象,当我为一张嘴唇涂上唇膏时,嘴唇忽然裂开而显出一个微笑时,我会怎么想,太多的记忆使我不能从事这一项与我非常相称的职业。
只是,如果我转换了一份工作,我的苍白的手脸会改变他们的颜色吗,我的满身蚀骨的防腐剂的药味会完全彻底消失吗?
那时,对于夏,我又该把我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绝对地隐瞒吗?对一个我们至亲的人隐瞒过往的事,是不忠诚的,世界上仍有无数的女子,千方百计的掩饰她们愧失了的贞节和虚长了的年岁。
这都是我所鄙视的人物。
我必定会对夏说,我长时期的工作,一直是在为一些沉睡了的死者化妆。而他必须知道、认识,我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所以,我身上并没有奇异的香水气味,而是防腐剂的药水味;我常常穿白色的衣裳也并非由于我刻意追求纯洁的形象,而是我必须如此才能方便出入我工作的地方。
但这些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些水珠罢了,当夏知道我的手长时期触抚那些沉睡的死者,他还会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跃过急流的涧溪吗?
他会让我为他修剪头发,为他打一个领结吗?
他会容忍我的视线凝定在他的脸上吗?
他会毫不恐惧地在我的面前躺下来吗?
我想他会害伯,他会非常害怕,他就像我的那些朋友。起先是惊讶,然后是不喜欢,结果就是害怕而掉转脸去。
怡芬姑母说:如果是由于爱,那还有什么畏惧的呢.但我知道,许多人的所谓爱,表面上是非常地刚强、坚韧,事实上却异常的脆弱、柔萎;吹了气的勇气,不过是一层糖衣。
怡芬姑母说:也许夏不是一个胆怯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对我的职业不作进一步解释的缘故,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完全是一个不擅于表达自己思想的人,我可能说得不好,可能选错了环境,气候、时间和温度,这都会把我想表达的意思改变.我不对夏解释我的工作并非是为新娘添妆,其实也正是对他的一种考验,我要观察他看见我工作对象时的反应,如果他害怕,那么他就是害怕了。
如果他拔脚而逃,让我告诉我那些沉睡的朋友;其实一切就从来没有发生。
我可以参观一下你工作的情形吗?
他问。
应该没有问题。
我说。
所以,如今我坐在咖啡室的一个角落等夏来。我曾经在这个时刻仔细地思想,也许我这样对夏是不公平的,如果他对我所从事的行业感到害怕,而这又有什么过错呢?为什么他要特别勇敢,为什么一个人对死者的恐惧竟要和爱情上的胆怯有关,那可能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已经亡故了,都是由怡芬姑母把我扶养长大的,我,以及我年轻的兄弟,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我对父母的身世和他们的往事所知甚少,一切我稍后知悉的事都是怡芬姑母告诉我的,我记得她说过,我的父亲正是从事为死者化妆的一个人,他后来娶了我的母亲。当他打算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曾经问她:你害怕吗?但我母亲说;并不害怕。
我想,我所以也不害怕.是因为我像我的母亲,我身体内的血液原是她的血液。怡芬姑母说,我母亲在她的记忆中是永生的,因为她这么说过:因为爱,所以并不害怕.也许是这样,我不记得我母亲的模样和声音。
但她隐隐约约地在我的记忆中也是永生的。
可是我想,如果我母亲说了因为爱而不害怕的话,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没有理由要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如此。或者,我还应该责备自己从小接受了这样的命运。从事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职业,世界上哪一个男子不喜爱那些温柔、暖和、甜言的女子呢?而那些女子也该从事一些亲切、婉约、典雅的工作。
但我的工作是冰冷而阴森、暮气沉沉的,我想我个人早已也染上了那样的一种雾霭,那么,为什么一个明亮如太阳似的男子要娶这样一个郁暗的女子呢,当他躺在她的身边,难道不会想起这是一个经常和尸体相处的一个人,而她的双手,触及他的肌肤时,会不会令他想起,这竟是一双长期轻抚死者的手呢。唉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原是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的。我想一切的过失皆自我而起,我何不离开这里,回到我工作的地方去,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叫做夏,而他也将忘记曾经认识过一个女子。是一名为新娘添妆的美容师。
不过一切又仿佛太迟了,我看见夏,透过玻璃,从马路的对面走过来。他手里抱着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一束花。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过生日吗。我看着夏从咖啡室的门口进来。发现我坐在这边幽暗的角落里.外面的阳光非常灿烂,他把阳光带进来,因为他的白色的衬衫反映了那种光亮。他像他的名字,永远是夏天。
喂,星期日快乐。
他说。
这些花都是送给你的。
他说。
他的确是快乐的,于是他坐下来喝咖啡。我们有过那么多快乐的日子。但快乐又是什么呢,快乐总是过得很快的。我的心是那么地忧愁。从这里走过去,不过是三百步路的光景,我们就可以到达我工作的地方。然后,就像许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一个失魂落魄的男子从那扇大门里飞跑出来,所有好奇的眼睛都跟踪着他,直至他完全消失。怡芬姑母说: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仍有真正具备勇气而不畏惧的人。
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假设,当夏从对面的马路走过来的时候,手抱一束巨大的花朵,我又已经知道.因为这正是不祥的预兆。
唉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是不宜和任何人恋爱的,或者,我该对我的那些沉睡了的朋友说:我们其实不都是一样的吗?几十年不过匆匆一瞥,无论是为了什么因由,原是谁也不必为谁而魂飞魄散的。夏带进咖啡室来的一束巨大的花朵,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他是快乐的,而我心忧伤。
他是不知道的,在我们这个行业之中,花朵,就是诀别的意思。